在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个夜晚,明尼阿波利斯市大湖街(Lake Street)一带的天空一直都火光冲天。
骚乱者烧毁了一家4S店(AutoZone)、一家手机店和一家餐厅(Town Talk Diner)。第二天晚上,他们破坏了一家人事代理公司、一家赛百味(Subway)和一家富国银行(Wells Fargo)储蓄所。仅仅72个小时,暴徒们打碎了玻璃,偷走了商品,并放火烧毁了数百家商店。
在大湖街往北两英里就是74岁老牧师约翰·派博的家,他可以看到升腾的黑烟,他像往常一样上床睡觉。
 “我睡的还可以。”他这样告诉福音联盟。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和他的妻子诺尔(Noël)感到害怕,他们自1980年以来一直住在这个资源不足的社区中,一栋简陋的房子里。他们知道如果听到枪声该怎么做(打911,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如何清理前廊上的十几根吸毒者遗弃的皮下注射针头(用扫帚扫起来,不碰它们),以及如何吓退闯入你家的人(开门大喊)。
“我睡的还可以。”他这样告诉福音联盟。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和他的妻子诺尔(Noël)感到害怕,他们自1980年以来一直住在这个资源不足的社区中,一栋简陋的房子里。他们知道如果听到枪声该怎么做(打911,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帮上忙),如何清理前廊上的十几根吸毒者遗弃的皮下注射针头(用扫帚扫起来,不碰它们),以及如何吓退闯入你家的人(开门大喊)。
派博四十年前搬进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复兴城市文明的宏伟愿景。他只是希望能步行上班,并认为住在教会所在的社区能让服事更真实。不久后,他坚信“存在于社区中对福音见证很重要”,于是发出号召,让伯利恒教会的成员加入他的行列。十年之内,这间教会中的400人在这个城市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买了房子。
 那是1980年的事了,那时生活在城市一点都不酷,远在2012年提摩太·凯勒出版《21世纪教会成长学》(Center Church)或2015年美南浸信会将“差派网络”(Send Network)的新教会植堂以城市为目标之前。在那时候,教会搬到郊区会有意义——离大多数成员更近、有更多发展空间——但伯利恒浸信会还是留在市中心。
那是1980年的事了,那时生活在城市一点都不酷,远在2012年提摩太·凯勒出版《21世纪教会成长学》(Center Church)或2015年美南浸信会将“差派网络”(Send Network)的新教会植堂以城市为目标之前。在那时候,教会搬到郊区会有意义——离大多数成员更近、有更多发展空间——但伯利恒浸信会还是留在市中心。
“城市需要教会,”派博说,“我们不应该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城市。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教会已经在这里待了111年。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如果我们走了,市中心这边就会失去一个福音派教会,更何况已经所剩无几了。”
派博教会的成员们在没有总体计划的情况下就搬进了城市,这既让人困惑(“我们应该怎么做?”),但同时恰好是《当帮助带来伤害时》(When Helping Hurts)一书作者后来的建议(从建立关系、观察和学习开始)。
每个人最后都做了不同的事情。但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在失望和挑战、抢劫和骚乱、破碎的玻璃和公园里无家可归的帐篷城中努力。他们至今仍然在这样服事。
随着乔治·弗洛伊德遇害的消息传开,塔吉特百货(Target)员工就开始收到公司短信,告诉他们不要进城上班。其中一位员工是牧师约翰·埃里克森的儿子,他们家就住在派博家对面。
“我当时就想,‘这是怎么回事?’” 埃里克森说,“然后我意识到抢劫已经开始了。周二到周三,这个城市变得毫无生气。周二、周三、周四都没有警察的存在,也没有消防的存在。我于是对教会的领袖们说,‘我们得做点儿什么。’”
 埃里克森几乎一辈子都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他的父母在1982年听到民权活动家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谈到搬迁到破碎地区的重要性后,就主动搬到了菲利普斯社区(Phillips)。虽然当时与派博住的地方只相隔六个街区,但埃里克森直到在加州读马斯特斯大学(恩典社区教会所办的大学)时才碰到派博,他形容当时的派博是个“野心勃勃的激进分子”,在大学的礼堂里讲道。埃里克森后来加入了伯利恒浸信会成为职员和牧师长达十年,在三年内植堂建立了两间教会。
埃里克森几乎一辈子都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他的父母在1982年听到民权活动家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谈到搬迁到破碎地区的重要性后,就主动搬到了菲利普斯社区(Phillips)。虽然当时与派博住的地方只相隔六个街区,但埃里克森直到在加州读马斯特斯大学(恩典社区教会所办的大学)时才碰到派博,他形容当时的派博是个“野心勃勃的激进分子”,在大学的礼堂里讲道。埃里克森后来加入了伯利恒浸信会成为职员和牧师长达十年,在三年内植堂建立了两间教会。
他现在仍然带领着第二家教会,禧年社区教会(Jubilee Community Church),这间教会就位于伯利恒浸信会以南不到三英里的地方,距离弗洛伊德遇害的地方仅一英里之遥。自2009年创立到如今,这间教会已经发展到175名成员,成员们像埃里克森一样深入到附近社区服事。例如,当他注意到周边社区没有少棒队——因为很多孩子都没有父亲,这就意味着缺乏教练——他开始了菲利普斯火蚁队。
在发生骚乱后的第三个晚上,“我们去了Target超市停车场,在那里搭起了一个祷告帐篷,”埃里克森说。当他问警察是否可以这样做时,得到的答案是:“这是一个战区。随你们……这可能会带来好处,但我们无法保护你们。”
因此,当人们闯入Target超市,抢劫了他儿子本来要进货和清点的商品时,埃里克森和他的教会分发瓶装水并邀请人们一起祷告。“我们和很多很多人进入了交谈,”他说,“我们教会的人开始来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帮忙清理。但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气氛很不稳定。我们知道——伙计,这必定会是个不眠之夜。”

的确是个不眠之夜。在禧年教会成员收拾东西离开后不久,有人在离他们原先站立的地方几英尺远的地方烧毁了一辆汽车,另一个人被刺伤。第三分局警署遭到占领和摧毁。
第二天晚上,埃里克森把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送回娘家,而他和大儿子则在家里观察和祈祷。他们拿出了花园里的水管,以防火势蔓延到他们的街区。埃里克森接到教会成员的电话,他们的问题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我的街区着火了,消防队不来了,我该怎么办?我想我需要疏散离开,但外面有太多人,我没法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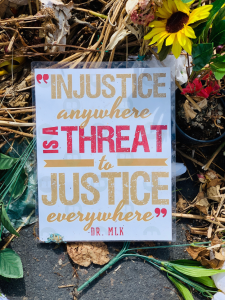 但即使是那些前往城外的家人或朋友那里避难的人,也在一两天内回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来自许多教会的基督徒一同清理碎玻璃,进行行走祷告,并在“耶利哥之路”——一个在禧年教会地下室向邻居提供食物和社会服务的组织——做志愿者。
但即使是那些前往城外的家人或朋友那里避难的人,也在一两天内回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来自许多教会的基督徒一同清理碎玻璃,进行行走祷告,并在“耶利哥之路”——一个在禧年教会地下室向邻居提供食物和社会服务的组织——做志愿者。
“我们觉得应该长期在这里,倍增门徒,”埃里克森说,“我们希望看到人们真正长期与耶稣同行,看到健康的教会建立起来。”
这意味着“在附近忠心耿耿,只是蹒跚前行,”他说,“每一天你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大成就。只是一点一滴,主在帮助我们。”
骚乱发生的当晚,在完成了一整天的服事后,杰夫·诺伊德正在修剪他的灌木。
这并不是说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冷漠无情——他能感觉到附近“压力越来越大”,就像“一个准备爆炸的火药桶”。他住在离大湖街三个街区的地方,他能看到黑烟,听到交火的枪声。
 “我真的希望晚上能和其他牧师一起在第三分局门口祈祷。”他说,但诺伊德的服事对象是那些资源不足的人,新冠疫情给这些人带来了很多艰难。他日夜不停地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甚至很多周末都得摆上,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真的希望晚上能和其他牧师一起在第三分局门口祈祷。”他说,但诺伊德的服事对象是那些资源不足的人,新冠疫情给这些人带来了很多艰难。他日夜不停地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甚至很多周末都得摆上,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因此,他只是把垃圾桶拉到车库里,这样就没人能在里面点火了。然后他做了一些不用动脑的体力劳动,这样他就可以放松他的大脑。
他修剪了他的灌木,因为它们长得有点太高了,而且也是因为他住在这个社区,并且打算长住。
诺伊德从1985年开始就一直住在菲利普斯,当时伯利恒开办了一个团契小屋(名为“koinonia”,希腊文“团契”之意),让年轻人住在一起,同时在这个社区传讲福音。
 然后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与她结婚了,在附近买了一套房子。然后,他只花了一美元就买下了旁边的房子,修缮了一下,租了出去。然后,他又结识了马路对面的邻居——他们是从卡特里娜飓风中撤离的人——甚至带着他们的孩子去边界水域(The Boundary Water)划独木舟。他看着这些孩子们归向了基督,仅此一个收获就让他愿意再做一次。
然后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与她结婚了,在附近买了一套房子。然后,他只花了一美元就买下了旁边的房子,修缮了一下,租了出去。然后,他又结识了马路对面的邻居——他们是从卡特里娜飓风中撤离的人——甚至带着他们的孩子去边界水域(The Boundary Water)划独木舟。他看着这些孩子们归向了基督,仅此一个收获就让他愿意再做一次。
诺伊德从事城市中心贫民区事工已经28年了。他带领着“耶利哥之路”,这事工是在禧年教会的设施里运作的。他和两名助手(以及大约30名志愿者)将人们与社会服务机构联系起来,帮助提供简历和国家身份证明,协助处理财务危机,并分发食物。即使在骚乱之前,新冠疫情就已经把2020年变成了异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3月份,我们分发了5万磅食物,”诺伊德说,“4月份,我们做了10.8万磅。5月,我们做了12.8万磅。”
当骚乱破坏了附近的杂货店后,“耶利哥之路”就在大湖街设立了食品货架供应有需要的人。现在,诺伊德和他的志愿者们正在努力解决下一个问题——向无家可归者在附近公园里搭建的数百顶帐篷发放水和卫生用品,因为6月份市政府宣布这些帐篷为避难场所。
 “一些(帐篷住户)是从城外来抗议的,然后留了下来,”诺伊德说,“有些人来自美国原住民保留地,把这看作是一个找工作和重新安置的机会。”他希望参与为他们寻找住房资源的服事。他们可住的地方之一是由前伯利恒教会成员、现在某个家庭教会成员吉姆·布鲁姆和塞西尔·史密斯购买并经营的综合公寓。(“他们服事附近最贫困的人,他们是按着国度价值观在进行管理,”他们的朋友拉斯·格雷格说,“多年来,他们已经服侍了数百人。”)
“一些(帐篷住户)是从城外来抗议的,然后留了下来,”诺伊德说,“有些人来自美国原住民保留地,把这看作是一个找工作和重新安置的机会。”他希望参与为他们寻找住房资源的服事。他们可住的地方之一是由前伯利恒教会成员、现在某个家庭教会成员吉姆·布鲁姆和塞西尔·史密斯购买并经营的综合公寓。(“他们服事附近最贫困的人,他们是按着国度价值观在进行管理,”他们的朋友拉斯·格雷格说,“多年来,他们已经服侍了数百人。”)
诺伊德还记得几十年前,当他告诉父亲他要搬进菲利普斯时,来自父亲的怀疑和反对。他的父亲并不反对帮助他人,但认为诺伊德可以仍然住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然后去帮助他人。
诺伊德承认,这样想也没错,他本可以这样做。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但与你服事的人住在同一个社区会给你一个独特的见识,”他说,“你就有机会参与街区俱乐部、参与周间查经,有机会看到枪击案、谋杀案和被盗的车辆。”
还可以看到警察的不公正、骚乱和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城,看到人们来到基督面前,看到人们获得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的家人,并最后在经济上自立。
“的确有困难的日子,相信我,”他说,“但总的来说,我会用这个词来描述这里的事工:这样的服事是一种特权。”
骚乱发生的当晚,拉斯·格雷格哭了。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天,”他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30年,看到城市的发展在一瞬间被摧毁,这着实令人心痛。”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菲利普斯一直在慢慢改善。在经历了60、70、80年代的白人逃离城市之后,伯利恒浸信会成员和其他人士的存在帮助稳定了这个社区。与此同时,廉价的住房吸引了难民——尤其是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逃离东非战争的难民,城市愿景(City Vision)的执行总监约翰·梅尔(John Mayer)说:“基本上是移民们重建了这个社区,是基督徒开始祷告和传福音,并关心人们。”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菲利普斯一直在慢慢改善。在经历了60、70、80年代的白人逃离城市之后,伯利恒浸信会成员和其他人士的存在帮助稳定了这个社区。与此同时,廉价的住房吸引了难民——尤其是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逃离东非战争的难民,城市愿景(City Vision)的执行总监约翰·梅尔(John Mayer)说:“基本上是移民们重建了这个社区,是基督徒开始祷告和传福音,并关心人们。”
今天,菲利普斯街头有100多种语言——最常见的是西班牙语和索马里语。各个族群的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6年,一座巨大废弃的西尔斯大厦被重新启用。现在这里是Alina Health公司总部、中城全球市场和住宅区的所在地。这里也是大部分骚乱发生的地方,全球市场的几十家企业被毁。
“就在我们的城市在骚乱中被摧毁的那个晚上,我们为高中毕业生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晚宴。”格雷格说。他20年前开始了这所学校,因为当时他听了派博讲道,说要为上帝冒险做一些‘有点疯狂’的事情。第二天,格雷格辞去了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最富有的郊区一所基督教学校发展总监的工作,在菲利普斯创办了一所基督教经典教育学校。
 二十年后,希望书院从教会地下一层35名学生发展到七层教学楼的500名学生。在这个有色人种儿童毕业率全美最差的地区,希望学院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操练美德,并获得大学奖学金。
二十年后,希望书院从教会地下一层35名学生发展到七层教学楼的500名学生。在这个有色人种儿童毕业率全美最差的地区,希望学院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操练美德,并获得大学奖学金。
“培养具有学术资格——但更多的是内心资格——仆人领袖对我们城市来说至关重要,”格雷格说。
当他们的社区遭到破碎和燃烧时,希望书院2020届毕业生在Zoom上聚会、庆祝他们的毕业,并听取他们每一位老师的致辞。每一位老师都在最后们告诉他们:“希望书院与你们的家人约定,要培养你们成为一个国度的公民。现在是你们为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种族和谐和喜乐合作而努力的时候了。请记住,耶稣来不是为了受人服事,而是为了服事人。”
“我们听到这句话21次,”格雷格说,“当我们祷告时,我们都在想,我们的城市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未来的领袖。那是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过去五个月的全球疫情、经济不确定性、种族不公和骚乱,会让人觉得上帝已经抛弃了菲利普斯。
 “但神没有。”格雷格说,“而且他甚至可能策划了这一切,以实现他国度的目的。”格雷格已经可以瞥见这一点——他的老师们与学生家庭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定期打电话询问情况。他们给一些人送去了杂货,花钱更换了另一个人的破冰箱,提供了硬币让另一个人可以使用洗衣店(因为通常提供硬币兑换的银行已经被砸烂了)。希望书院还设立了一个新冠疫情救济基金,帮助家庭解决学费问题,收到了近10万美元的捐赠。
“但神没有。”格雷格说,“而且他甚至可能策划了这一切,以实现他国度的目的。”格雷格已经可以瞥见这一点——他的老师们与学生家庭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定期打电话询问情况。他们给一些人送去了杂货,花钱更换了另一个人的破冰箱,提供了硬币让另一个人可以使用洗衣店(因为通常提供硬币兑换的银行已经被砸烂了)。希望书院还设立了一个新冠疫情救济基金,帮助家庭解决学费问题,收到了近10万美元的捐赠。
接下来格雷格会努力给市议会成员打电话,介绍帐篷城的情况。营地里的肮脏注射器、性侵犯和暴力意味着菲利普斯的孩子们不能在公园里玩耍。自7月以来,大多数帐篷已经被拆除了。
“在我们街区尽头,有30个帐篷在一块空地上。希望书院旁边的公园里还有10到12个帐篷。”格雷格说,“前几周,一个18岁的孩子在那个公园里被枪杀了。感觉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战区。”
但格雷格留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场只能以一种方式结束的战争。
“神必然得胜,”他说,“国度必然得胜。我所做的是充满希望的冒险,爱是我这样做的理由。……在接下来的四到五个月里,看到神如何使用他在这里安插的子民去爱、去服侍、去以重要的方式带领,这将是很有趣的。”
火灾发生的那晚,佟明璟并不在菲利普斯。虽然他在那里住了十年,后来搬到了城北的另一个社区。
但身为伯利恒社区福音拓展牧师的佟明璟,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了菲利普斯。
 有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和他家一起捡碎玻璃。“我就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个活动,主要只是在自己的页面上分享给附近的人。”他说,“一个小时内,我的活动就得到了1200次分享。这真是太疯狂了。”
有朋友给他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和他家一起捡碎玻璃。“我就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个活动,主要只是在自己的页面上分享给附近的人。”他说,“一个小时内,我的活动就得到了1200次分享。这真是太疯狂了。”
一小时后,当他见到他的朋友时,又有400人来参与了。
“这只是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双城附近的人,”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们做了一堆清理工作。因为我做了10年的街区清理工作,我知道该怎么做。”(包括了打电话给存放手套和袋子的五金店老板,向市政府索要黄色垃圾袋——这表示垃圾已经被志愿者收集起来,垃圾车将免费收集。将装满的袋子堆放在路边。)
第二天早上,暴动带来的破坏更加严重,而且从大湖街蔓延到更远的地方。明璟和他的朋友尼克·斯特罗姆崴(Nick Stromwall)去了教会,并建立了一个“支持城市”的网页。
“我们基本上是说:我们做这个网页是为了帮助人们知道损失在哪里,需求在哪里,以及你可以去哪里获得帮助,” 明璟说,“在五天之内,我们有近22000名追随者。从Facebook的统计数据来看,我想我们动员了大约8000人参加我们创建的30个活动。”(他们还推广了其他人发起的活动。)
 “支持城市”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正好填补了一个需求。但佟牧师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地行动,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邻居们的需要、听他们讲故事,了解谁能帮助什么。(他是如此地乐于助人,以至于当他邻居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时,他要求佟牧师在他入狱后收养他的儿子。)
“支持城市”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正好填补了一个需求。但佟牧师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地行动,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邻居们的需要、听他们讲故事,了解谁能帮助什么。(他是如此地乐于助人,以至于当他邻居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时,他要求佟牧师在他入狱后收养他的儿子。)
过去的那份忠心是人们信任他现在还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多年来,伯利恒浸信会一直为移民开办ESL(教外国人英语)事工,帮助没有车的移民买菜,和提供社区圣经学习,并与当地邻里协会合作清理垃圾、解决安全问题,以及举办节日活动。
“我们的方法论,至少在我的领导下,就是参与和服务,并通过建立关系来分享好消息。” 佟牧师说。他知道这一点做得并不完美,但“我们不能因为做不对而什么都不做。”
佟明璟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与我们附近的其他组织建立联系,”他说。这一点很重要——伯利恒浸信会并不是唯一在菲利普斯开展服事的团体。多年来,他们经常与其他教会或组织合作。佟牧师参加联合会议、去参加社区领袖们的聚会,并与官员商讨土地使用或住房开发的策略。
“我的整个生活都是为了拓展福音,”佟牧师说。他鼓励住在菲利普斯的教会成员将服事未信主的人纳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并在这一路上成为福音之光。“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活的祭物。”
硝烟弥漫的大湖街还不足以把派博赶出这个社区。
有人砸坏了他的车,有人偷了他儿子的自行车。几周前,一个男孩问他是否可以帮忙割他家草。派博说“可以”——当一个孩子想要工作赚点零花钱时,他总是这样支持。但后来那个男孩带着另一个朋友回来了,并试图撬开窗户。“诺尔和我坐在五英尺远的地方,看着他们这样做,”他说,“后来我打开门,他们逃跑了。”
 几天后,派博听到一声撞击声,看到一辆汽车撞上了人行道。司机下车向一个人开枪并且打伤了他。“他的手流了很多血,”派博说,他接着拨打了911。
几天后,派博听到一声撞击声,看到一辆汽车撞上了人行道。司机下车向一个人开枪并且打伤了他。“他的手流了很多血,”派博说,他接着拨打了911。
“这些年来,我最大的争战之一就是不要变得狭隘,”派博说。比起成功,他更能感受到失败。“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我们在美国本地社区的影响似乎很小。”伯利恒浸信会也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多种族和多元化。社区犯罪仍然很常见——在最近这个季节更是如此。
不过,也有这样的时刻:
“几个礼拜前,我坐在后院的野餐桌旁吃午饭,”派博说,“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停下来说,‘嘿,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你还住在这里啊!我小时候经常在你的车道用弹弓打水桶。人们常告诉我说,我住的社区很糟糕,我会告诉他们——这不可能!牧师就住在街角。’”
派博总结说:要量化长期存在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是相当困难的。
同时,以福音为中心的期望也很重要。
“当我读到《彼得前书》时,”派博说,“彼得对被赢得基督的人的期望似乎并不包括去转变文化。圣经期望是:继续宣扬那召你之神的美善之处、继续服事。有些人会被你感动以至于信靠基督,也有些人则会继续恶言相向。”
派博接着说:“彼得说话不像一个城市重建专家。他使用了诸如‘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前1:6)、‘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彼前2:12)、‘忍受冤屈的苦楚’(彼前2:19)、‘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前4:12)等短语。”
换句话说,《圣经》并没有应许,如果你搬进像菲利普斯这样的社区,人们就会放下毒品和暴力、追求赞美诗的歌声和稳定的家庭结构。
 “但他们可能会看到你的行为,并将荣耀归给神。”派博说,“你的工作就是在那里,爱他们、宣讲真理,解释你所怀盼望的缘由。我的工作就是忠心,神的工作是多结果子。我们想看到果子,但果子不是我们留在城里的理由。”
“但他们可能会看到你的行为,并将荣耀归给神。”派博说,“你的工作就是在那里,爱他们、宣讲真理,解释你所怀盼望的缘由。我的工作就是忠心,神的工作是多结果子。我们想看到果子,但果子不是我们留在城里的理由。”
他比以前少了很多担心被人利用的感觉。“以前我自诩能看穿谎言,让人在讨钱的时候说话自相矛盾。”他说,“但渐渐地,主让我明白,在审判日,精明没有奖赏,爱才有奖赏。而耶稣的命令则是:要转过脸去让人打、要把你的衣服都给人、要走两里路而不是只走一里路,这些都让我知道,被人利用是正常的。”
“耶稣关注的是杀死我的自私,多过关注谁得到了多少钱。我的问题应该是:我在基督里面会不会得到满足,所以被人利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这个社区附近工作了40年,如果重来一次,派博认为自己还是会这样选择。“我真的相信,十年又十年地传讲神的全备真理,建立一个奉献生命的教会,时不时地领受呼召为耶稣做一些疯狂的事,以这位伟大的神所教导的神学为支撑,以及成为这间城市中存在的榜样,这些都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于是他不断雇佣孩子们修剪草坪,在附近慢跑时派发新约圣经,与无家可归者交谈。在弗洛伊德遇害后的几周内,诺尔每天都去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大友谊宣教浸信会的食物分发处做志愿者。而附近的其他基督徒则带领社区俱乐部,种植社区花园,捡拾垃圾,在公园区做义工,和邻居们一起祷告。
“如果当有人对我说,‘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居住,那会是哪里?’我会说,‘诺尔在哪里?’”派博说,“其次,我会问,‘哪里有需要?’”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iots in John Piper’s Neighborhood